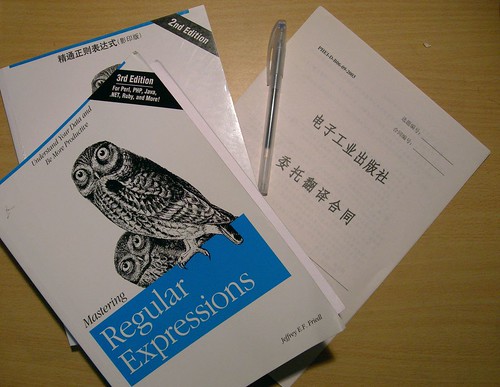王老师
题记:“记住,一定要把技术练好,这才是你的安身立命之本”,这是我离校的时候,他给我的忠告。当时只觉得他是一片好心,现在才真正体会到,那岂止是一片好心,更是一片苦心。今天的状态,希望没有辜负他的苦心+好心。
2002年9月的一天晚上,我下自习看见数学楼的橱窗里贴着一则告示——《关于中文系开设副修专业汉语言文学的通知》。当时,我正处在饥渴而兴奋的茫然之中,之前两年的阅读,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的思想和观念,已有的世界被颠覆了,新的知识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,却没有新的秩序和能力来梳理它们。我苦苦找寻,然而除了时间一天天流逝,一无所获。这个偶然的机会,在当时显得魅力无穷,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,它的确改变了我的大学。
第二天去中文系办打听,知道要交六百块钱,不过可以试听第一节课。跟家里申请经费的时候,父亲说,只要觉得好,就去,不用在乎这点钱。
第一节课是周六的晚上,中文系201,狭长的教室。老师个子不高,虽然说不上具体的年龄,但可以肯定不超过四十岁。从包里拿出水杯,放到讲台上,就开始上课。
“事先都不知道,系里就安排我给参加副修班的同学讲第一堂课。我姓王,给大家讲文艺理论”。
说完,他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。两个字说不上龙飞凤舞,也说不上苍劲有力,甚至有些绵绵的感觉,透出别致的韵味。
然后,他从“文艺学”的概念开始讲起。
“文艺学这个概念,来自苏联;如果按照字面的意思,应该翻译成文学学,为了保持通顺,改叫‘文艺学’。”
“文艺学是研究文学本身的学问,它的成果叫文艺理论,或者文学理论……广义的文学理论包括文学史论,文学批评,和文学理论,这其中,只有文学理论是最直接地指向文学本身的,因此,它也叫作狭义的文学理论。”
……
我必须承认,那是我上大学以来,甚至是这些年以来听过的,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课。我第一次知道,课讲得好,可以好到这种程度——不但让人完全丧失了时间的概念,反而被一种获取知识的愉悦所充实,源源不断。(多年以后,我读到亚里士多德说的,人天生就有求知的欲望,知性的快乐所带来的充实感,是其它乐趣所无法比拟的,心有戚戚焉。)
“太值了!”
“要来听!”
那天晚上,和历史系的几个朋友一起走在回来的路上,我们都兴高采烈,满心欢喜。
交了钱,我们很快就发现,虽然三位老师分别教授不同的科目,但只有王老师的课讲得最好,来听的人最多,也最平易近人。
那时候,我们总有无穷多的问题,无穷多的想法;因此,课间的休息成了我们跟他讨论的宝贵时间。现在想来,很多问题确实很幼稚,但他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一点反感,总是用最平实的语言娓娓道来。
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,他说话的时候会不时地把目光从提问的人身上移开,环顾所有聚在身边的人,这其中饱含我从未感受到的尊重和怜爱,总是让我倍加感动。
一天晚上,下了课,我缠住他:“王老师,您说说,信仰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,我现在越想越想不明白了?”
“这个问题,我想是这样的……”
他说了很多,听的很过瘾。出了中文系的门,还没有说完,却不得不打住——他要径直走,穿过正对中文系的小门回家,我不好继续纠缠,只好垂头丧气地往回走。
正在这时,他又从后面叫住了我,“你等一等,门没开,我们可以继续聊”,接着赶了上来。
当时已经是10月底了,长春的天很冷,但我心里是暖呼呼的,我们边走边聊,一直走到自由大路与人民大街的交界处,他说“太晚了,你要回宿舍了,下次再说吧”,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
其实,我已经能够感觉到他对我很好,非常好,比对别的同学要好。当时,我猜测,这是因为自己是副修的学生中唯一一个来自理科院系的缘故。
有次上课,他提到符号美学,提到恩斯特·卡西尔的《人论》——“这本书很好,我自己的借给一个朋友,被弄丢了,我只好自己骑车去学人书店,又买了一本”。第二周课间的休息,我走上去说“王老师,您上周提到的那本《人论》,我也买了一本,看了一半,有些想法……”。
那天之后,我们的关系似乎就有些微妙了。
有一次,他在课堂上讲到阿里斯托芬:“阿里斯托芬,阿里斯托芬,你们知道阿里斯托芬是什么人吗?”
“喜剧作家”,“悲剧作家”,“文学家”……,大家的回答不一。
“剧作家”,我回答说。
“呵呵,你最狡猾,不确定是喜剧作家还是被剧作家,你就给出一个不会错的答案。”他笑了,指着我说。
当然,我也不是只会这样投机取巧,印象中有好几次,他提的问题,我都能飞快地答上来。
“不错,这样上课的感觉非常好”。他对这种默契的赞许,几乎能让找回小时候的得意劲儿。
到后来,每次课间的时间,包括从下课到走出校门的时间,几乎是专属于我的,我们谈的话题也不局限于文艺,哲学,科学,历史,都有涉及。
有一次课间,他走过来,问:“你最近在看什么书?”
“启良的,中国文明史,从朋友那借的。”
“哦,启良,我知道,看过他的《东方文明畅想录》,这个人应该算个解构主义者……”
……
“王老师,我最近看了一本《鲁迅传》,好多想法啊。”
“哦,谁写的?”
“王晓明。”
“王晓明?他很善于讲故事,很多时候用诗化的语言,感染力很强。”
……
学期结束了,我很不甘心,失去这样的讨论机会,于是跑去中文系看教授坐班答疑的安排,总是在周三的上午跑去他的办公室,经常看不到任何一个学生去请教,心中窃喜——因为,这些时间都属于我。
其实,也许这说不上“讨论”,但我仍然固执地认为那不是一种单纯的解答和应付,而是用心的,有共鸣的交流——有天晚上聊天时,他对我说,“朋友是不分年龄限制的”,那句话,印象无比深刻。
但是,这样的讨论,终究不可能如上课时那般频繁了,到了大三,我开始准备GRE和TOEFL,而他也调任学生处,很少在系里坐班了。
“你要注意,千万不要把真理的逻辑,直接套用到现实中来”,有一次,下班的时间,我去学生处找他聊,他跟我说“我在系里,大家还多少讲些真理的逻辑,但是在这里,事情完全不一样了。”
到了大四,这样的机会就更少了,他总是很忙,很忙;整个那一年,我只去找过他两次,是因为我不敢。
04年寒假过后的一天晚上,我下了自习从图书馆出来,见到校门口的花坛,在暗黄的灯光和松树的映衬下,如同巨大的灵堂。那一刻,真是把我怔住了。
想想王老师,已经忙于行政工作,我不再有机会跟他讨论智慧和真理的话题了;政法学院的孟老师,不堪排挤去了南京,我也不再有机会去他家里畅谈终日了。整个学校,值得我寄托和留念的,能够让我向往的,只剩下夜幕中的图书馆了。
临离校的时候,他送我一本书,是新出版的,他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,并题了一句话作为留念:XX同学,祝你前程似锦,愿你相信存在。
那本书,我一直随身带着。
天冷了
气温一天比一天低了,今天的最高温度,似乎也只有不到10度,我却依然骑车穿行在城市的车流中。
身体似乎一天比一天更好了,一条牛仔裤,两件衣,就已经足够;我甚至可以只穿一件衬衫,走在街上,遇到路人怪异的目光。
读书时穿的那些衣服,通过一个教会的朋友捐给了贫困地区。捐出去前我试穿了几件,依稀可以找到在学校时的影子,其实是因为,每一件衣服都有记忆的;可惜,没有留影。希望,它们现在能给新的主人带来温暖。
下班以后,去固定的西饼屋买蛋糕当晚餐,接过蛋糕的那一瞬间,我忽然想到《重庆森林》里的某个镜头,感觉惊人的相似。
今天很偶然地见到一双鞋,是我喜欢的样式,穿上也很舒服,在根本不了解Scholl这个品牌的情况下买了。回来一查,才知道这还是一个“令美丽与舒适首次交融的百年英国经典品牌”。
看来,我还真是够孤陋寡闻的。

又是一万字
从礼拜一晚上到现在,又出了一万字的翻译稿。
每天晚上将近三个小时,三千字左右,速度还算不错,让我满意的是,这一万字几乎就是定稿,不需要太大改动了。
白天上班,C++, Python, PHP, MySQL, Lighttpd,搞得我头都要大了;晚上看《领导开发团队》和《敏捷数据》(终于把《如彗星划过夜空》看完了,重温一遍美国制宪的历史,感觉还不错),然后是翻译。居然没有乱套,我自己也有点吃惊。
今天比较郁闷的事情是,下午稀里糊涂的时候,错敲了一个命令,把一台服务器的root分区干掉了,导致各种奇怪的问题。回家才想明白,明天还得去恢复:(
在混乱中齐头并进
在学校时,曾有个一起上自习的朋友对我说,你怎么能同时看那么多书,而且互不干扰,真不知道你的大脑是怎么构造的。
那句话,印象深刻。
现在,手头也是一堆事情,要考虑的东西更多,虽然很多都没理出头绪,好歹也做到了互不干扰,至少重要的事情没有受到干扰。
在混乱中齐头并进,就是我目前的感觉。
寻找黄金时代
很意外地知道了这个片——寻找黄金时代,找来看了。
背景音乐是舒缓的手风琴,天然就有一种亲切感(惭愧的是,我已经三个礼拜没有碰过我的琴了);
云南的农场里,黄澄澄的油菜花,一片片的,看起来尤其舒服;
面对镜头,王小波憨厚腼腆的表情,随意但充满智慧的言说,无比可爱。
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小波的视频,却有一种深深的伤感。不知道为什么,每次想起这个片,我总是想到鲁迅《伤逝》中的那句话:她的命运,已经决定她在我所给与的真实——无爱的人间死灭了!
死灭,这个怪怪的单词,倒是最真切地表达了这种心情。
P.S.
我忽然想到,寻找黄金时代,翻译成英文,应该是这样
Tracing Gold Times
搞了一天的SWIG
需要用到最新的中文语言分词SDK,接过来是C++的,我已经很久不写C++,差点都忘记了。
更要命的是,这套软件本来是在Win32下开发的,后来才转到UNIX/Linux平台下,连命名方式都是Win32的风格:匈牙利命名法,各种让我眼花缭乱的宏。
面对各种诡异的问题,两眼抓瞎,Google又总是断,只能用Yahoo来搜索……
忙到现在,总算是用SWIG把这东西包装好了,可以直接用Python调用,再写成一个服务,以后就不用操心这种事情了。
幸亏今天搞定了,要不会郁闷到晚上睡不着的。
无尽压力此中来
高三时,班主任老师曾说,大家不要把高考想的太可怕,觉得高考好像座山一样慢慢压过来,这种心态要不得…….
当时,我从未有过那种感觉;倒是现在,出于兴趣(或许有点追名逐利的打算也说不定),接了这个翻译的事情,有了这种感觉。每天上班劳心劳力,已经很疲惫,晚上还要折腾文字;礼拜五给我的感觉,不再是马上有两天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欣喜,倒是离交稿日期又近了一周的紧迫。